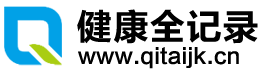
2020-02-08
癌症免疫治疗已经成为治疗肿瘤重要的方案。鉴于大量的临床前研究和临床研究致力于推进内源性 endogenous和合成 synthetic免疫治疗方法,确定肿瘤免疫提供确切疗效获益的障碍进一步发展对基础研究的认识和促进临床转化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2020年1月14日发表于 Immunity 的论述中,Daniel Chen及其基因泰克前同事 Priti S.Hegde定义了癌症免疫治疗面临的十个关键挑战,从将临床前的发现转化为临床实践策略,到为任何给定的病人确定最佳的基于免疫的治疗组合。应对这些挑战将需要基础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的共同努力,并需要集中资源,以加快对癌症与免疫系统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的了解,并为癌症患者开发改进的治疗方案。
十大挑战
1. 为深入研究人体肿瘤免疫特征机制建立可靠的临床前模型
2. 探索揭示肿瘤免疫的主要驱动因素
3. 理解肿瘤免疫的器官特异性
4. 理解导致原发免疫逃逸和二次免疫逃逸(耐药)的分子和细胞机制
5. 阐述内源性 endogenous和合成 synthetic免疫治疗的异同
6. 在早期临床研究中精确评估肿瘤免疫联合策略的有效性
7. 对使用类固醇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治疗自身免疫性毒性而产生的对肿瘤免疫效果的影响进行全面评估
8. 通过精细的生物标志物评价系统来最大化个体化肿瘤免疫的效能
9. 为肿瘤免疫的临床研发制定改良的评估终点
10. 应用抗肿瘤免疫联合策略来最大化长期生存获益
由于临床前模型中的肿瘤微环境在免疫细胞的组成,肿瘤新抗原,和由于慢性炎症或和抗原暴露导致的免疫细胞抑制的复杂性,目前使用的临床前标本或不能反应人类肿瘤的肿瘤微环境情况。
比如结直肠癌MC38小鼠模型来自致癌物的暴露,携带有较高的肿瘤突变符合,反映了CRC的一种超突变/微卫星不稳定状态,但这种情况在人类CRC中较少见 ≤5%。而CT26 结直肠癌模型为非超突变或微卫星稳定肿瘤模型,但携带有重组内源性逆转录病毒抗原,也具有较强的免疫原性。
CT26合成肿瘤模型中可见大量的细胞毒性免疫细胞浸润,而MC38 或EMT-6模型中则可见大量的免疫抑制细胞成分,包括MDSCs,T细胞则被排除在外。
在这种情况下,基因工程小鼠模型最能代表人类疾病。传统上,这些模型是通过敲除肿瘤抑制基因或以器官特异性的方式使用CreLoxP系统诱导体细胞突变来产生新生肿瘤。但是由于这种方法产生的肿瘤并未模拟真实情况下突变积累和肿瘤的进化演变过程,所以倾向于表征免疫原性较低的“冷肿瘤”,而往往对免疫治疗的疗效反应欠佳。
Kersten, K., de Visser, K.E., van Miltenburg, M.H., and Jonkers, J. (2017).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ouse models in oncology research and cancer medicine. EMBO Mol. Med. 9, 137–153.
肿瘤细胞(肿瘤微环境)与免疫系统存在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特别是与启动和激活、细胞毒性活动和调节以及记忆反应的形成相关的相互作用,突出了除了剂量选择外,还需要了解治疗的排序和计划。这样的治疗优化在临床试验中进行测试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测试的组合的数量是惊人的。应用新的技术和方法能够更好的反应人类肿瘤的biology和对免疫应答的机制至关重要。
根据tumor immunity continuum的分类描述法,针对不同免疫原性的肿瘤微环境进行表征,需要精心筛选合适的临床前模型来验证符合人类肿瘤中的关键特征的治疗假设。
Figure 1. The Tumor Immunity Continuum
inflamed肿瘤(炎症性肿瘤环境)通常被定义为,肿瘤细胞表达PD-L1,且肿瘤区域有较多的免疫细胞和TiLs浸润的情况。从组织学检测中可以看到T细胞在间质区域密集散步,并且与肿瘤细胞有密切接触和连接(突触)。出上图中提示的可以表征肿瘤微环境免疫原性状态的标志物(PD-L1表达,TMB,IFNγ信号通路的表达,et al),近期的研究提示,肿瘤局灶中的B细胞可能参与了T细胞介导的肿瘤免疫。那些带有浆细胞样B细胞浸润的肿瘤往往从免疫治疗中获得更好的生存获益。
Griss, J., Bauer, W., Wagner, C., Simon, M., Chen, M., Grabmeier-Pfistershammer, K., Maurer-Granofszky, M., Roka, F., Penz, T., Bock, C., et al. (2019). B cells sustain inflammation and predict response to 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 in human melanoma. Nat. Commun. 10, 4186.
由MSI或TMB状态所代表的基因组不稳定性产生了可被MHC分子锚定的新生抗原,是一种高度的“异己信号”。总体来说,在肿瘤形成早期阶段的突变分布在几乎所有的肿瘤细胞中(克隆突变)对比更晚出现的branch mutation 可能产生更强的T细胞应答效应,后者仅在一部分肿瘤细胞中存在(亚克隆)。
Mosely, S.I., Prime, J.E., Sainson, R.C., Koopmann, J.O., Wang, D.Y., Greenawalt, D.M., Ahdesmaki, M.J., Leyland, R., Mullins, S., Pacelli, L., et al. (2017). Rational Selection of Syngeneic Preclinical Tumor Models for Immunotherapeutic Drug Discovery. Cancer Immunol. Res. 5, 29–41.
近来,从NSCLC 的Checkmate-227 和 MYSTIC研究分析结果看,TMB对于生存获益的提示作用可能扑朔迷离, Peters et al., 2019a; Peters et al., 2019b, 但鉴于肿瘤发展过程中由于杂合缺失机制(LOH)导致的免疫编辑事件的存在,对这一问题尚不能盖棺定论。通过人HLA基因位点上的LOH突变导致的抗原呈递的机制缺失,可能影响T细胞对恶性肿瘤的有效识别。
Figure 2. Qualitative Overview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Immune Phenotypes and TMB Across Cancer Types
那个“异军突起”的高突变负荷的免疫沙漠就是小细胞肺癌了。诸多二线及以上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临床研究已经前赴后继,折戟沉沙,比如checkmate 331, checkmate 451, keynote 604。神经内分泌瘤包括SCLC在内,显示出低TiLS浸润特征,多为免疫沙漠表型。
Carvajal-Hausdorf, D., Altan, M., Velcheti, V., Gettinger, S.N., Herbst, R.S., Rimm, D.L., and Schalper, K.A. (2019).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PD-L1, B7-H3, B7-H4 and TILs in human small cell lung Cancer (SCLC). J. Immunother. Cancer 7, 65
理论上,T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是靶向多种抗原表型的,并且针对特定抗原表型(比如肿瘤)的重要免疫反应具有随机性,导致反应性T细胞在活化,动员,刺激扩增和生存上存在一定的竞争性。已经有多项报道指出存在在肿瘤微环境中的浸润T细胞,或多为“旁观者T细胞”bystander,不能对肿瘤抗原起效应的“吃瓜群众”。但针对特定抗原的T细胞反应决定了抗肿瘤免疫反应的深度和持续时间。
实际上,由于肿瘤存在广泛的瘤内异质性,瘤间异质性,鉴别出针对特定抗原的T细胞反应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考虑到种种T细胞刺激活化的随机性和肿瘤微环境的复杂情况。Linnemann et al., 2014; Scheper et al., 2019; Rizvi et al., 2015; Jamal-Hanjani et al., 2017; McGranahan and Swanton, 2015; Joshi et al., 2019
尽管病毒感染状态与肿瘤对免疫治疗的疗效反应之间的关系尚无定论,但已经有研究证实某些病毒的基因组可能整合进宿主的基因组从而导致染色体不稳定。(Flippot et al., 2016)。在某些没有很高的肿瘤突变负荷的肿瘤中,仍然存在着infamed的表征。比如RCC 肾透明细胞癌 或肝细胞癌。RCC中有较高的人内源性逆转录病毒的存在,并且在这类肿瘤中能够观察到T细胞针对hERVs的应答作用。Smith et al., 2018。其他的一些肿瘤与某种特定的病毒感染史有关,比如EBV病毒,乙肝病毒,人乳头状病毒或者莫克细胞多瘤病毒。
immune-excluded 肿瘤是指能够在肿瘤微环境中清晰观察到T细胞在肿瘤间质区域滞留,并且TGFβ信号高表达,髓样细胞浸润,和活跃的血管生成。(Galon and Bruni, 2019; Hegde et al., 2016; Hugo et al., 2016; Mariathasan et al., 2018)。越来越多的证据提示,TGFβ通路参与了这种特殊肿瘤微环境的形成。
一些转化研究分析的结果提示TGFβ通路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这种免疫表型的形成。在EMT6乳腺癌模型中用aPDL1联合aTGFβ方案成功将这一表型逆转为炎症性免疫表型 (Mariathasan et al., 2018)
针对这一策略的联合方案正在进行临床研究测试。 (NCT02734160, NCT04064190, NCT02947165)
在肿瘤发展初期,促进肿瘤生长的原动力来自于原发器官的内在特性。
Fig. 1 | The cellular and architectural heterogeneity of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at distinct cancer sites.
Salmon, H., Remark, R., Gnjatic, S., and Merad, M. (2019). Host tissue determinants of tumour immunity. Nat. Rev. Cancer 19, 215–227
在转移性尿路上皮癌的免疫治疗应答中,存在着两种迥异的应答模式,肝脏的转移灶倾向于对治疗产生抵抗,淋巴结的转移灶对治疗有更好的应答。(Balar et al., 2017; Massard et al., 2016; Rosenberg et al., 2016; Tumeh et al., 2017; Pillai et al., 2016)
肝脏是已知的免疫豁免器官。
病灶所处的器官环境影响病灶的应答。
Fig. 2 | Cellular contributors to tissue-specific antitumour responses
不同解剖部位的血管通过表达不同水平的黏附分子、黏附性和周细胞覆盖率来不同程度地控制肿瘤免疫浸润,调节免疫细胞外渗。虽然人们对淋巴管对癌症免疫系统浸润的不同影响了解甚少,但现在已经确定的是,淋巴管通过促进对自身抗原的耐受性、将抗原保存以备后用以及抑制效应免疫应答来帮助形成免疫反应。癌症相关的成纤维细胞通过分泌趋化因子、细胞因子、生长因子和活性氧来调节抗肿瘤免疫反应,并产生和重塑基质,为免疫细胞提供导向和屏障功能。新出现的证据表明,共生细菌可以通过刺激免疫细胞分泌炎性细胞因子等方式,在系统和局部两方面为抗肿瘤免疫反应奠定基调。组织驻留细胞,包括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和记忆T细胞,通过直接作用于肿瘤细胞或调节浸润免疫细胞,有助于形成抗肿瘤免疫反应。神经细胞通过释放神经递质和生长因子影响肿瘤细胞的存活、血管生成和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的功能。
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单药或联合,有超过半数以上的患者不会对治疗产生有效应答,即便是在那些最初由应答的患者中,绝大多数也会产生耐药和疾病进展复发。前者称为“原发免疫逃逸”,后者称为“二次免疫逃逸”。从参与多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临床研究病例标本中进行的多组学分析正在试图揭示免疫逃逸的机制。如前所讨论的,由TGFβ信号通路参与的免疫耐药现象在膀胱癌中已经被生动描述。
这些肿瘤表现出致密的胶原原纤维,它们将T细胞困在间质室中,阻止T细胞参与和杀死肿瘤细胞。至少在临床前,联合抗pdl1和抗tgfb抗体可以部分克服这种逃逸机制。
鉴于抗VEGF在MDSCs重编程中作用的丰富数据,以VEGF为靶点来克服MDSC介导的免疫抑制似乎是合理的,在肝癌和透明肾细胞癌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抗血管生成的治疗已经获得了成功。
二次逃逸在CAR-T细胞治疗和新抗原特异性T细胞治疗领域也有充分的文献记载。在前者中,CAR靶向的肿瘤抗原的丢失已被证明与临床效益的丧失有关,正如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CD19 CAR Ts的丧失一样 (June et al., 2018; Grupp et al., 2013)
现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基础是endogenous immune response, 即通过阻断PD-1或者PD-L1,解除T细胞的抑制发挥其杀伤作用。(Chen and Mellman, 2013; Herbst et al., 2014; Tumeh et al., 2014)
但是许多肿瘤细胞通过下调MHC-I类分子或干脆删失来逃避免疫失败和编辑。
synthetic immune response 通过人为的将T细胞与肿瘤细胞拽到一起,而不依赖于MHC分子来校正这种逃逸机制。CAR-T和CD3双特异性抗体都属于此类治疗。(June et al., 2018; Zhukovsky et al., 2016)
CAR-T细胞代表从患者中分离出来的转基因T细胞,通过人工操作导入与肿瘤相关的抗原相互识别结合的区域,该抗原识别区域通常与TCR信号蛋白和T细胞共刺激蛋白相连。CAR - T细胞的有效性依赖于CAR - T细胞浸润到所有的肿瘤解剖位置,特异性结合和杀伤恶性细胞,以及CAR - T的存活和/或原位增殖,直到所有的恶性细胞被清除,所以在实体瘤领域尚未突破治疗瓶颈。
Carl H. June, et al.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herapy. NEJM,2018
Samaha和同事最近的一份报告提出了CAR t细胞治疗实体瘤——胶质母细胞瘤的临床前研究的成果(动物模型,老鼠,米奇)。这些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表达一种归巢分子(一种粘附分子)CAR-T细胞来,这种分子允许CAR-T细胞与构成血管系统的内皮细胞结合(类似通行证的作用),然后在胶质母细胞瘤小鼠模型中通过内皮细胞进行迁移。他们的方法建立在对肿瘤内皮表型和影响t细胞内皮移植的粘附途径的详细研究上。
Marion H. Brown, Ph.D., and Michael L. Dustin, Ph.D.Steering CAR T Cells into Solid Tumors.N Engl J Med 2019; 380:289-291
CD3双特异性抗体通常包含一组包含CD3蛋白结合域和一个肿瘤表面抗原结合域的融合蛋白,能够特异性的介导T细胞识别和杀伤表达相关抗原的肿瘤细胞。CD3双特异性抗体发挥作用依赖于人体天然的浸润T细胞。
桥联细胞是一种重要的特有作用机制,双特异性抗体(bsAb)使两类细胞物理上靠近,导致效应细胞在靶细胞存在时排他性激活。例如,双特异性效应细胞可使细胞毒性T细胞或自然杀伤(NK)细胞重新定向(retarget))杀伤肿瘤细胞。这个概念也被用于通过桥接肿瘤抗原与免疫检查点在肿瘤微环境中(重新)激活T细胞免疫。在感染性疾病中,利用bsAbs对T细胞进行重定向以消除病毒感染细胞,或者阻断病毒感染细胞的通路(比如埃博拉病毒bsAb通过结合病毒表面的糖基蛋白和病毒binding site 的裂解糖基蛋白,阻断埃博拉病毒进入细胞质)。b, c |受体细胞的桥接(独联体)是一种交联特定细胞表面受体导致其失活(例如,减少肿瘤生长在癌症应用程序)或激活(例如,有条件地激活生长因子受体治疗糖尿病)专性机制。d | BsAbs可以被设计成精确定位酶和底物作为一种辅助因子模拟物,例如在血友病治疗中替代关键凝血因子的bsAb。e, f |“背驮”允许一个易位手臂携带活性绑定分子进入到难以进入的结构, 如转运药物蛋白进入中枢神经疾病血脑屏障,或阻断细菌或病原体逃脱。
Aran F. Labrijn, et al. Bispecific antibodies: a mechanistic review of the pipeline.Nat Rev Drug Discovery, 2019
当然可以理解,CD3双特异性抗体介导的synthetic免疫高度依赖于肿瘤细胞表面表达相关抗原,是一种相对特异性的肿瘤免疫疗法,需要精确选择和筛选此类抗原以最大化抗肿瘤效能。
目前在临床试验阶段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疗法多达上千种,急需要可靠的方法学来对其成功的可能性在早期临床研究阶段即进行精确评估,以免过多消耗医疗和研发资源。
类固醇激素对 免疫 系统有直接作用,能够影响T细胞和B细胞的功能。对不同T细胞亚群的效果不同,最终结果是导致外周循环中的T细胞数量减少。(Olnes et al., 2016)
因此,激素在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GVHD(宿主排异),以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引起的AE方面扮演着重要的治疗作用。
尽管目前的证据看起来,因为CPI-AE而接受激素治疗的病人似乎也能从CPI 治疗中获得可持续的肿瘤应答,和生存获益。(Freeman-Keller et al., 2016; von Pawel et al., 2017; Weber et al., 2017). 在临床上,那些需要接受激素预处理的化疗和CPI联合方案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功(KEYNOTE189, KEYNOTE407).
类固醇多大程度上实际上削弱了抗癌免疫反应,最有可能受到应用时机(早期和晚期),剂量,时间表,和特定的应用模式(高与低剂量类固醇,连续与间歇与单一类固醇剂量,使用类固醇的效力),和使用类固醇时肿瘤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答情况。对其他形式的免疫抑制的进一步研究甚至更加有限。
See document(s): 三碗不过岗,主要看身板儿!NSCLC免疫治疗疗效差,激素该背锅吗?
在肿瘤医生面对病人时,最先蹦到脑子里的问题是:“针对他们的具体疾病,最佳的治疗方法是什么?”今天,癌症患者的诊断测试还没有完全融入到临床实践中;检测率从7%到50%不等, 在不同的癌症类型中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Chawla et al., 2018)。虽然这种现状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教育和获得有效诊断检测平台的途径,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缺乏临床证据支持医生的决定有关。在免疫治疗中尤其如此。
关于biomarker的论述和文章犹如恒河沙数,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也实在整理不动了,下面两个文章链接作为推荐阅读)
传统的统计和临床研究终点已经用于PDL1/PD-1抑制剂的适应症开发审批,使许多这些药物快速获得广泛的临床应用批准(例如,pembrolizumab、nivolumab、atezolizumab、durvalumab和avelumab (Tang等,2018)。然而,这些端点,包括ORR、PFS和OS,并不能完全满足研究CPI临床疗效和获益的需求。对于大多数转移性癌症患者和他们的治疗医生来说,他们的目标是达到CIT的持久反应和生存。在检验Kaplan-Meier生存曲线时,通过“曲线的尾部”来衡量和表征这种获益(Chen,2013)。然而,目前衡量这种益处的临床试验方法缺乏,分析不够有力,需要长时间的随访,通常持续数年(Gauci等,2019年),比如5年生存率。此外,ORR评估没有考虑到CIT可能导致反应延迟(如肿瘤持续生长后肿瘤缩小)或“假进展”(如由肿瘤炎症引起的明显肿瘤生长后肿瘤缩小)(Hodi等,2016;Wolchok等人,2009)。PFS的评估同样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因此,已经开展了定义和验证更好的CIT终点的综合尝试,包括制定免疫相关反应标准(Wolchok et al., 2009)、实体肿瘤免疫反应评价标准(RECIST) (Seymour et al., 2017)、免疫修饰的RECIST和免疫修饰的PFS (Hodi)et al.2018)。不幸的是,验证需要大量的数据集和反复核实确认,最终可能只是针对某一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进行优化验证。OS评估可能是更适合CIT疗效评估的重点,尽管它可以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完成,需要治疗的患者完成一定的死亡事件,并收到对照组交叉到治疗组的影响,且在一定的人群中存在交叉。其他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终点包括使用基于模型的生长速率常数估计来预测OS效益(Claret et al., 2018)、里程碑OS、加权log-rank OS或使用基于cox模型的time varying treatment effect estimate(Hodi et al., 2018a;Lin和Leo ' n, 2017)。需要继续整合和优化CIT评价终点。
联合治疗的总体目标是避免重叠的毒性,最大化协同抗肿瘤效应,最小化重叠的耐药机制的可能性。鉴于整个免疫循环(immune cycle)上的组合可能性可能数以千计,亟需开发出一种更新颖的临床研究模式以便更快更优先甄别出有效的治疗方案。(Nass et al., 2018)
这种新颖的设计包括已经广为人知的伞式试验和篮式试验。这些试验设计是适应性的,允许新的组合,药物剂量,和/或联合用药的时间表被迅速添加到试验中,并为患者提供灵活的切换组合。总的来说,这些临床试验设计可以促进更快、更有信心的决策制定,也可以连续地将治疗方法添加到一个方案中,或者相反地,连续地解构复杂方案的组成部分。
包括durvalumab联合olaparib的I-SPY (NCT01042379),MORPHUS 和FRACTION研究。(Chau et al., 2018; Simonsen et al.,2018)
The concept of consilience, a
unity of knowledge—but not necessarily thinking—is a particularly apt description of what is now necessary: bridging scientists, collaborative groups, and ideas (Graeber, 2019)
推荐阅读
文章评论
注册或登后即可发表评论
登录/注册
全部评论(0)